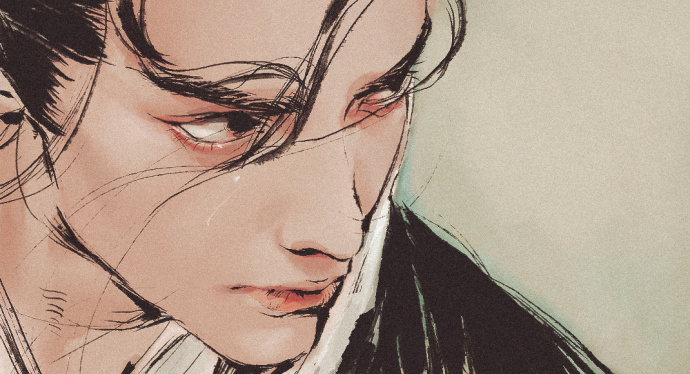夜,是败犬的遮羞布,也是饿狼的猎场。
刘猛那伙人,就是一群在西大街土道上亡命的败犬。恐惧像一条无形的鞭子,狠狠抽在他们屁股上,两条腿蹬得比纺车轮子还快,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。
而王啸天,就是那头缀在他们身后,不把猎物撕碎誓不罢休的饿狼。
他的肺像是两个被捅破了的风箱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的刺痛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胸腔里那颗心脏疯狂地擂着鼓,仿佛随时要从喉咙里跳出来。他不知道自己追了多久,只知道眼前昏暗的街道开始扭曲、旋转,脚下的步子越来越沉,像是灌满了铅。
终于,在追出不知几条街后,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也被榨干。他眼前一黑,像一截被砍倒的木桩,直挺挺地扑倒在地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狼狈的身影消失在夜色深处。
他趴在冰凉的土地上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喉咙干得像是要烧起来。
撑着旁边冰冷的墙壁,他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。
月光惨白,像给死人脸上扑的粉。墙上,一行用白石灰刷的大字,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刺眼,像一个巨大的、冰冷的烙印,狠狠烫在他的视网膜上:
【新婚夫妇入洞房,计划生育不能忘!】
嗡!
王啸天脑子里那根紧绷到极限的弦,在看到这行字时,彻底断了。
他茫然地环顾四周。红砖砌成的筒子楼,低矮破旧的土坯房,还有远处传来的、若有若无的迪斯科音乐……这条街道,这个年代独有的气息,像潮水般将他淹没。这不是梦,也不是幻觉。
不远处,一家新开的游戏厅门口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,里面传来“叮叮当当”的电子音效和少年们的叫嚷声。那声音像一盆凉水,将王啸天从混沌中浇醒。
他渴,渴得要死。
他拎着那把还在滴血的菜刀,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。刀尖滴落的鲜血格外瘆人。
游戏厅门口,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小青年正靠在门框上,一手插兜,一手举着一瓶橘子味汽水,得意洋洋地看着里面的人打拳皇。
王啸天面无表情地走到他面前。
小青年感觉到光线被挡住,不耐烦地抬起头:“干啥?…天哥,你……你别激动,是我,浩子!”浩子的脸瞬间白了,那股子浓重的血腥味,熏得他差点尿了裤子。”
眼前这个他熟悉的王啸天,此时却无比的陌生,浑身散发着浓得化不开的血腥气。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,就像两块在冰窖里冻了千年的石头。更让他魂飞魄散的,王啸天手里拎着的一把还在往下滴血的菜刀。
王啸天没有说话,只是伸出手。
浩子甚至没敢问他要干什么,身体已经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。他哆哆嗦嗦地将手里的汽水瓶递了过去,牙齿上下打着架,发出“咯咯”的声响。
王啸天一把夺过汽水,仰头“咕咚咕咚”地灌了下去。冰凉的、带着甜味的液体划过他着火的喉咙,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他将空瓶子随手一扔,玻璃瓶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“看到刘猛了吗?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摩擦。
“没 ,没有”浩子带着哭腔答道。王啸天得到了答案,没再看他一眼,转身就走。他的背影在游戏厅闪烁的灯光下拉得又长又诡异,像一个从地狱归来的孤魂。
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,浩子才“嗷”的一声,腿一软,瘫坐在地上大叫起来。游戏厅里的人听到动静探出头来,看到这一幕和地上的血迹,吓得赶紧缩了回去,把门都给关上了。
王啸天回到家门口时,看到了台阶上那个蜷缩着的身影。
是许艳。
刚才还像一头发了狂的母豹子的女人,现在却像一只淋了雨的幼鸟,抱着膝盖,在清冷的夜风里瑟瑟发抖。她的身上披着一件王啸天的旧外套,显得那么单薄。
她不是怕那帮流氓回来,她是怕他。怕他真的杀了人,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;怕他刚刚燃起的那点男人血性,会把他送上绝路,也毁了她刚刚才看到的那么一点点希望。
听到脚步声,许艳猛地抬起头。
当她看到王啸天那一身尚未干涸的血污时,那双勾人的狐狸眼瞬间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水雾。她再也忍不住,不管不顾地冲了过来,紧紧抓住他的胳膊,声音都在打颤:“你……你没伤着哪儿吧?”
她的手心滚烫,充满了鲜活的温度。 “没事。”他摇了摇头。
“人呢?你……没把他们怎么样吧?”许艳的声音带着哭腔,眼神里满是后怕。
“想来着,”王啸天咧了咧嘴,露出一口白牙,只是那笑容在血污的映衬下显得有些狰狞,“没追上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”
咣当!
他手一松,那把沉重的菜刀掉在地上,发出一声脆响,像是给今晚这场荒唐的闹剧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“那就好……跑了就好……”许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,整个人都软了下来。她随即又上下打量着他,那张梨花带雨的脸上,竟慢慢绽开一个笑容,既有劫后余生的庆幸,又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野性光彩。
“笑什么?”王啸天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。
“笑你啊,”她伸手,用指尖轻轻戳了戳他结实的胸膛,那里还沾着尿骚和血迹,她却丝毫不在意,“我让你砍,你就真敢下死手?你这头闷声不响的老黄牛,发起火来,是真敢顶死人啊!”
“以后,”王啸天看着她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有我在,这个家,就没人敢再欺负。”
许艳的眼神闪烁了一下,没再多问,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两人进屋,打水,清理地上的血迹,换下脏污的衣服。等一切尘埃落定,窗外的天际已经泛起了一抹鱼肚白。
新房里,一切又恢复了原样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“你上炕睡吧,累了一晚上了。”王啸天坐在炕沿边,点上一根不知从哪儿摸出来的烟,看着已经换上干净睡衣的许艳。
“你不睡?”许艳上了炕,宽松的衣料也遮不住她那惊心动魄的玲珑曲线。这个女人,就像一坛最烈的烧刀子,是个男人都想一口闷了。
“我给你守着,”王啸天的神经还紧绷着,几十年的窝囊气一朝宣泄,他只想睁着眼,好好看看这个失而复得的世界,守着这个失而复得的媳妇儿,“怕那帮孙子杀个回马枪。”
“他们不敢。”许艳却摇了摇头,她的声音很轻,却异常肯定,“现在,他们比谁都怕你。上炕来,睡吧。”
王啸天迟疑了一下,没有动。
“怎么?”许艳看着他,“嫌我被刘猛那畜生碰过,脏了?”
“没有!”王啸天猛地抬头,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许艳定定地看了他几秒,忽然朝他伸出手,那双在昏暗灯光下亮得惊人的眼睛里,没有欲望,只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和坚定。
“那就上来。”她轻声说,“啸天,我累了,也怕。上来抱着我睡,行吗?”
王啸天看着那只向他伸出的、干净而温暖的手,沉默了片刻。他掐灭了烟,脱掉鞋,爬上炕,躺在了她的身边。
许艳立刻像只寻求温暖的猫一样,钻进了他的怀里,将头埋在他的胸口。
“从今往后,”她在他怀里闷声说道,“你就是我许艳的爷们儿,唯一的爷们儿。”
王啸天僵硬的手臂,终于缓缓抬起,将她紧紧地、紧紧地抱在了怀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