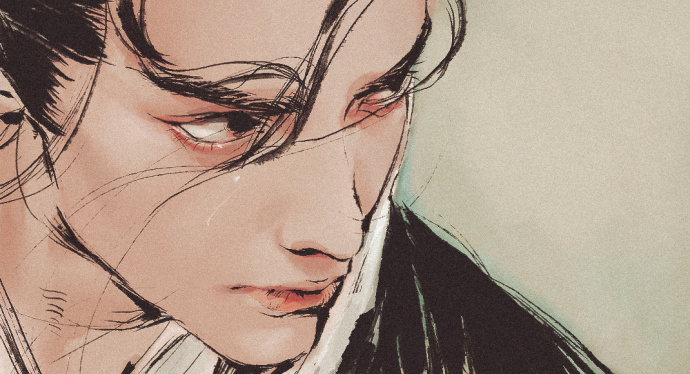泥土的芬芳,混着鞭炮残留的硝烟味,是王啸天对这个新婚夜最踏实的记忆。
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,他刚刚痛快地放了水,一身轻松。堂屋里透出的灯光,昏黄却温暖,像一块融化的麦芽糖,把他整颗心都黏住了。屋里头,是他刚用八抬大轿抬进门的媳妇儿,许艳。
一想到许艳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和笑起来的浅浅梨涡,王啸天这个三十年没跟女人大声说过话的庄稼汉,脸上就烧得厉害。他搓了搓冰凉的手,怀揣着一股新奇又胆怯的喜悦,推开了院门。
不对劲。
屋子里太吵了。不是亲戚们闹洞房那种善意的哄笑,而是一种粗野放肆的狂笑,夹杂着酒嗝和男人们不堪入耳的荤话。许艳的声音呢?怎么一点都听不见?
王啸天心里猛地一沉,像坠了块秤砣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堂屋门口,一把推开虚掩的木门。
“谁……”
他的话只来得及出口一个字。门后阴影里,一根粗壮的木棍带着风声,结结实实地砸在他的后脑勺上。
眼前金星乱冒,世界瞬间天旋地转,最后映入眼帘的,是地上几双不属于他的、沾满泥污的胶鞋。随即,他便一头栽倒在地,彻底失去了意识。
……
冷。
刺骨的冷意从水泥地面渗上来,像无数条冰冷的毒蛇,钻进王啸天的四肢百骸。脑袋里像被塞进了一窝马蜂,嗡嗡作响,每一次心跳都牵动着后脑勺针扎似的剧痛。
一股浓烈的酒气和劣质烟草味呛得他几欲作呕,更让他胃里翻江倒海的,是一股温热的液体正浇在他的脸上和脖颈里。那股骚臭的气味,让他瞬间明白了是什么。
“哈哈,猛哥,你看这怂货,尿他一脸都不带醒的!”
“老实人就是好欺负,你看他那死狗样!”
“快看炕上,猛哥要办正事了!让这新郎官好好听听声儿!”
屈辱!
无法言喻的屈-辱像烧红的铁水,瞬间浇遍了王啸天的全身!他用尽了毕生的力气,才终于将沉重如铁的眼皮撑开一道缝隙。
屋里的一切,都像一场扭曲的噩梦。
窗上大红的“囍”字,此刻看来像一道道流血的伤口。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正围着他,其中一个叫“麻子”的混混,甚至还嚣张地抖了抖裤腿,满脸的嘲弄。
他的视线艰难地转向那铺着大红鸳鸯被的火炕,下一秒,他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冻结了。
村里的混混头子刘猛,正赤着上身,像一头肥硕的种猪,将他新过门的媳-妇儿许艳死死压在身下。许艳那身崭新的红嫁衣被撕开了一大片,露出雪白的肩膀。她像一只被捕兽夹夹住的狐狸,拼命地抓挠、撕咬,喉咙里发出困兽般嘶哑的嗬嗬声。
当许艳的目光扫到地上刚刚苏醒的王啸天时,她那双原本美丽的眼睛里,最后一点希冀的光也熄灭了,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绝望和鄙夷。
“王啸天!”她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,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,狠狠扎进王啸天的心窝,“你答应过要对我好的!你答应过要护着我的!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被这帮畜生欺负吗?!”
炕上的刘猛动作一滞,狞笑着回头,一口黄牙在灯下闪着油光:“喊什么?你男人就是个窝囊废!小美人,别急,哥哥这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男人!”
说着,他那只肥腻的大手就要去扯许艳最后的遮羞布。
“你……是个男人……就去厨房拿刀!”许艳的哭喊变成了命令,带着一种玉石俱焚的疯狂,“杀了他们!王啸天!给我杀了这帮杂种!”
杀了他们……
杀了他们!
这四个字像一道惊雷,劈开了王啸天脑中所有的混沌和懦弱。老实人,不是没脾气,只是那根弦埋得比别人深。而此刻,这根弦,被名为屈辱和愤怒的烈火,彻底烧断了!
“吼——!”
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从王啸天的喉咙深处炸开!他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牛,猛地从地上弹起,满是污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,一双眼睛里布满了骇人的血丝。
“哟,诈尸了?”
“还敢瞪眼?弄死你!”
那几个混混被他这一下惊得后退半步,但随即又围了上来,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明晃晃的匕首。
王啸天没有理会他们,而是转身,用一种近乎撞墙的姿势,一头冲进了相连的厨房!
“操!这孙子真要玩命?”
“怕个球!他一个种地的,还能翻天?”
话音未落,王啸天已经再次冲了出来。他手里,多了一把用来剁猪骨头的厚背砍刀,刀刃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森然的冷光。
“来啊!有种往这儿捅!”那个叫“麻子”的混混梗着脖子,把匕首往前一递,脸上满是挑衅。
“爷们儿!砍死他!”许艳的声音就是扳机!
“我-日-你-妈!”
王啸天将胸中所有的屈辱、愤怒、恐惧全都灌注到了这一声咆哮里。他整个人像一张拉满的弓,手臂肌肉坟起,那柄沉重的砍刀划过一道毫无章法的、却充满了原始力量的弧线,对着麻子那张丑恶的脸,狠狠劈了下去!
噗嗤!
那不是刀砍在骨头上的脆响,而是一种砍进湿木头里的沉闷声响。
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秒。
“啊——!”
杀猪般的惨嚎撕裂了夜空。麻子脸上从眉骨到嘴角,一道深可见骨的血口子猛然绽开,皮肉外翻,鲜血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。他捂着脸,像一袋破麻袋般瘫倒在地,疯狂地抽搐打滚。
“真……真他妈砍了!”另一个混混吓得双腿一软,手里的匕首都掉在了地上。
炕上的刘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停了手,满脸的不可置信。
就在这一瞬!
许艳眼中爆发出惊人的狠厉,她蜷起的膝盖如毒蛇出洞,用尽全身的力气,对准刘猛毫无防备的裆部,闪电般地狠狠一顶!
“嗷——!”
一声比麻子还要凄厉百倍的惨叫炸响,刘猛捂着要害,像一只被开水烫了的虾米,弓着身子从炕上滚了下来,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“畜生!你去死!”许艳发了疯,翻身下炕,对着还在地上抽搐的刘猛的头和背就是一顿猛踹,嘴里还在尖叫:“爷们儿!别停下!继续干他们!”
“爷们儿来了!”
这一声“爷-们儿”,像是一剂滚烫的烈酒,瞬间点燃了王啸天全身的血液!他不再是那个连说话都会脸红的庄稼汉,他是一个被侵犯了领地的雄狮!他再次举起滴血的砍刀,对着那帮已经吓傻了的混混,如虎入羊群般冲了过去!
“疯了!这小子疯了!”
“快!架上猛哥,快跑!”
这帮平日里横行乡里的恶霸彻底崩溃了。他们敢耍横,可从来没见过这种不要命的疯子!
“跑……”刘猛疼得脸都绿了,被两个小弟架着,连滚带爬地第一个冲出了门。
剩下的人如蒙大赦,屁滚尿流地跟着往外跑。
麻子最惨,他刚挣扎着爬起来,就被追上来的王啸天一刀砍在后背上,惨叫着扑倒在门槛外。
“操-你妈的!别跑!”
王啸天拎着刀,浑身浴血,像一尊从修罗场里爬出来的杀神,咆哮着追了出去,他的怒吼声,在寂静的村庄里久久回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