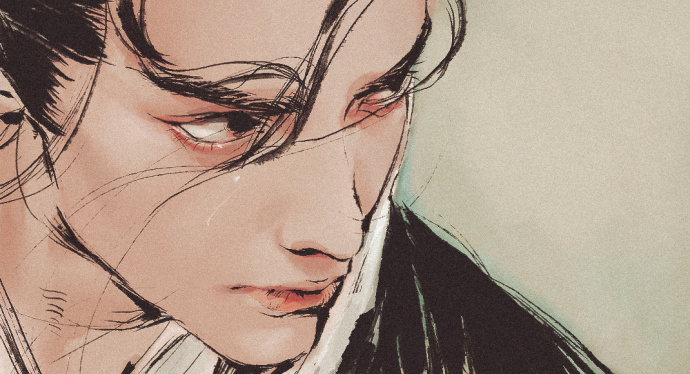那一夜的酒,喝到天亮。三个男人没说太多话,但有些东西,比话语更重。
太阳照常升起,西大街的天,却悄然换了颜色。 “王啸天”这三个字,像一阵风,刮过了这条街的每一个屋檐和角落。曾经那个提起来都让人觉得晦气的名字,如今却带上了一股子血腥味和敬畏感。人们谈论他时,声音会不自觉地压低,称呼也从“王啸天”,变成了又敬又怕的“天哥”。 踩刘猛,废孙五,这个曾经见了狗都要绕着走的软蛋,用最原始、最野蛮的方式,撕碎了过去的自己,也撕裂了西大街旧有的秩序。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,是他用八千块钱,就让孙屁眼连夜卷铺盖滚蛋,顺手接下了那家游戏厅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打架斗殴,这是赤裸裸的“吞并”。 王啸天没浪费时间。
从刘猛那儿来的一万块,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。游戏厅被彻底翻新,墙刷得雪白,破凳子换成了带靠背的新椅子。最关键的,是崔浩通过他那个跑海船的舅舅,从广州搞来了几台屏幕更大、灯光更炫的“奔驰宝马”老虎机。 “啸天游戏厅”开业那天,鞭炮从街头一直放到街尾,炸出的红纸屑铺了厚厚一层。
街坊邻里,但凡有点头脸的,都来了。份子钱不多,十块二十块,是个心意,更是个态度——承认你王啸天,是个人物了。
中午,王啸天在街上最大的“迎宾楼”摆了十几桌。他带着大胖和浩子,端着酒杯,一桌桌地敬酒。他话不多,但眼神沉稳,举手投足间,已然有了几分大哥的气场。 生意,毫无悬念地火了。
新机器的诱惑力是致命的,每天从早到晚,小小的游戏厅都挤得水泄不通。不光是西大街的混子,就连市里那些穿着喇叭裤、戴着蛤蟆镜的时髦青年,也蹬着自行车,穿越大半个城市,跑来一睹“天哥”的风采。
崔浩摇身一变成了“浩哥”,负责看场子和维护机器;大胖什么也不用干,就往门口一杵,那二百多斤的体格,就是最有效的“门神”。 这晚,游戏厅里又爆了满,连空气都燥热了几分。
王啸天搬了把椅子,坐在门口纳凉,翘着二郎腿,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喧嚣。
一群荷尔蒙无处安放的半大孩子,像苍蝇一样围着他,眼神里全是小弟对大哥的狂热崇拜。
“天哥,以后我跟你混了!”
“天哥,有事儿您说话,上刀山下火海!” “操!”王啸tian吐出一口烟圈,笑骂道,“都是街坊,说那些屁话干啥?以后在外面,别惹事,也别怕事。真遇上摆不平的,报我王啸天的名!不好使,再回来找我!”
“得嘞!天哥牛-逼!”一群小子嗷嗷叫唤。 就在这时,一个略显尴尬的身影,从街对面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。
是杨大春,那个不久前还被他用铁锹拍得满地找牙的壮汉。 “哟,春哥!”王啸天笑着站了起来,没提旧事。
“嘿嘿嘿……”杨大春搓着手,脸上是一种混合了敬畏和谄媚的复杂表情。他从兜里掏出十块钱,硬要往王啸天手里塞,“小天……不,天哥!你开业那天厂里加班,没赶上,今天补上,别嫌少!”
王啸天推辞不过,只好收下。他心里清楚,这杨大春无事不登三宝殿。 果然,杨大春又递上烟,亲手给他点上,姿态低到了尘埃里。
“春哥,有事儿直说,别跟我绕弯子。”王啸天懒得跟他客套。 “嘿嘿,还真有点事儿……”杨大春把他拉到一边,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哼,“厂里,出大事了。”
“嗯?”
“厂里那条往火车站送货的运输线,被人给‘盘’了!”
“盘了?什么意思?”王啸天皱起了眉。 “就是北郊那伙跑运输的,为首的叫王拐子。”杨大春眼里布满血丝,恨得牙痒痒,“他们把路给占了,说以后厂里所有的货,都得由他们的车队来拉。运费比原来高三倍!咱们厂自己的车要是敢上路,他们就见一辆砸一辆!前天,李师傅的车就被他们砸了,人也被打断了腿!” 王拐子。
听到这个名字,王啸天眼神一凝。当初许家死活不同意他和许艳的事,就是想把许艳嫁给这个在北郊倒腾走私货的“大能人”。 “报官没用?”
“没用!人家说这是运输公司之间的‘商业纠纷’,让咱们自己协调!这他妈哪是竞争,这就是拦路抢劫!”
“那你找我……” “天哥!”杨大春猛吸一口烟,“现在厂里几百吨的钢材堆在仓库里运不出去,合同交不了货,厂子就得赔大钱!再这么下去,厂子早晚得黄!厂子黄了,咱们这条街,大半的人都得喝西北风!”
“这道理我懂,可这事儿轮得到我管吗?” “天哥,是牛厂长让我来找你的!”杨大春终于把底牌亮了出来,“厂长说了,这事儿官面上解决不了,只能喝‘江湖茶’。他听说了你的事,觉得你是个有本事、讲义气的汉子,想请你出面,跟那伙人‘谈谈’。你现在名头响,他们兴许能给你个面子。” “我?”王啸天差点笑出声。他一个刚出道的小混子,凭什么? “厂长说了,只要你能把这事儿摆平,让厂里的运输恢复正常,厂里愿意出一万块‘协调费’!”杨大春又补了一句,声音更低了,“而且……你爸现在在厂里打更,万一哪天晚上……那帮孙子,下手可黑着呢!” “靠!”
王啸天骂了一句。
他听明白了,这是萝卜加大棒,把他架在火上烤。用他爹来拿捏他,这姓穆的厂长,也不是什么好鸟。 “天哥,算哥求你了!”杨大-春的姿态,近乎恳求。
王啸天沉默了。
最终,他点了点头:“行吧。”
他不是为了什么狗屁厂长,也不是为了那一万块。他是为了他自己。他知道,想在这西大街真正站住,光靠狠不行,还得有人心。
护住这条街所有人的饭碗,他王啸天,才算真正地站住了。 …… 第二天,浩子就把消息摸了回来。
那伙人的头儿,就是王拐子。巧的是,王拐子最近经常在容江大街新开的KK舞厅露面。 又过了一天,王啸天在厂长办公室,用那台金贵的黑色电话,通过一个倒爷,联系上了那位“贼王”。
电话一通,就传来一个懒洋洋、带着浓重匪气的声音。
“谁他妈找我?”
“王大哥您好,我叫王啸天……”
“谁?王啸天?”电话那头明显一顿。
“对,是我。”
“许艳那个废物男人?”
“……是。”
“操,你找我干几把毛?”
“王大哥,你看这样行不行?你定个时间地点,我请你吃顿饭。事儿成不成另说,主要是想跟您交个朋友。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随即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:“哈哈哈哈……操-你-妈的,你这小-逼-崽子还挺会来事儿!行!哥给你这个面子!今晚九点,容江大街,KK舞-厅!记住了,多带点钱!” “啪”的一声,电话挂了。
王啸天的眼神逐渐冰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