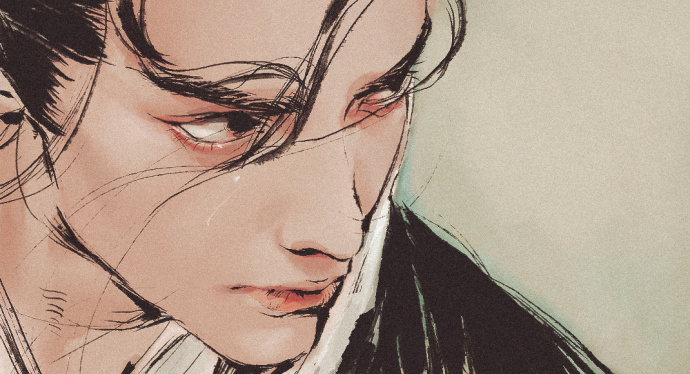天,亮了。
但西大街,比往常亮得更早。
天刚蒙蒙亮,根本不用杨大春去挨家挨户地敲门,整个西大街的混混儿,包括那些在厂子里上班、昨晚没赶上热闹的工人子弟,在听到“天哥被捅了”的消息后,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来,黑压压地聚集在了“啸天游戏厅”的门前。
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怒和兴奋,仿佛一场盛大的节日即将来临。
杨大春站在一把从游戏厅里搬出来的破椅子上,放眼望去,人山人海,而且还在不断地有人加入。他清了清嗓子,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即将检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。
“都别吵吵了!”杨大春扯着脖子,用他那独有的、充满“文化气息”的腔调喊道,“兄弟们,静一静!听我老杨,说两句!”
熙熙攘攘的人群,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几百双年轻而狂热的眼睛,齐刷刷地盯着他。
“昨晚舞厅的事,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!大铁桥的马大嘴,欺我天哥重伤在床,下战书要天哥的命!这口气,咱们西大街的爷们儿,能咽得下去吗?”
“不能!”
“干他妈的!”
“让他们有来无回!”
几百号人山呼海啸般的回应着,声浪几乎要掀翻整条街的屋顶。
“好!”杨大春非常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,他压了压手,继续道:“但是!大家听我说,咱大嫂有令,此去赴宴,只要十个人!十个最能打、最不怕死的兄弟!每人,一百块安家费!”
这话一出,人群瞬间就炸了锅。
“龙哥,凭啥只要十个人啊?”
“就是!我们都是西大街的,凭啥不让我们去?”
“我不要钱!让我去!我第一个上!”
“龙哥,必须有我呀!”
一阵阵的喧闹中,人群开始疯狂地往前挤,都想站到杨大春的面前,生怕自己落选。
“都他妈给我安静!”杨大春见场面有些失控,急中生智,再次清了清嗓子,摇头晃脑地大声吟诵起来:
“兄弟们,听我言!人多不一定顶尖!
大嫂用兵讲精悍,十员猛将破铁关!
不是不让大家上,时机未到别添乱!
谁敢不听军令状,就是跟咱天哥……对着干!”
这首比昨天更“文采飞扬”的打油诗一出,虽然依旧狗屁不通,但最后那句“对着干”却像一盆冷水,浇在了所有人的头上。没人敢再吵吵了。
“好!”杨大春见镇住了场面,立刻开始点将:“大迪!彬彬!你们俩,算两个!”
被点到名的两人,立刻昂首挺胸,从人群中挤了出来。
接着,杨大-春又陆续点了八个平时在西大街打架最狠、出了名的不要命的硬茬子。
这十个人,就是西大街最精锐的“敢死队”!
没被选上的人虽然一脸不甘,但也都没再闹事,因为他们知道,更重要的任务还在后面。
最后,杨大春又撇出了一句话:“现在,所有兄弟都回家睡觉,晚上八点,准时来这儿集合!”
数百人,渐渐散去……
中午十二点多。
医院里,王啸天的病房门并没有关,而是虚掩着。
门口,一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青春美少女,左手拎着一个精致的礼品盒,右手抱着一束鲜花,正犹豫不决。
就在这时,打开水回来的许艳,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站在门口的女孩。她愣了愣,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,故意把脚步放得很轻,走到女孩身后,才突然开口:“姑娘,找谁啊?”
“啊!”女孩被吓了一跳。她回过头,看到许艳,脱口而出:“我……我找天哥。”
“你是他朋友?”许艳上下打量着女孩。
“嗯,算是吧!”
“那进来吧!”许艳没有多问,伸手推开了门,一边向里面走,一边故意用一种夸张的语调,朝着床上的王啸天喊道:“小天啊,快醒醒!你的小情人儿来看你了!”
“啊?”王啸天被吵醒,有些诧异地睁开眼,就看到了一张纯净又带着惊慌的俏脸。是昨晚那个女孩,李雪!
“你怎么来了?”王啸天有些诧异地问。
“天……天哥你好,我……我来看看你,你……你怎么样了?”李雪被许艳那句“小情人儿”说得满脸通红,说话都磕巴了。
“吆,还真是英雄救美啊!”许艳把暖水瓶重重地放在桌子上,阴阳-怪气地说道,“小姑娘,坐啊,别客气。”
说着,她也不等李雪反应,直接从她手里接过了礼盒和鲜花,随手就扔在了旁边的空床上,然后一屁股坐在了王啸天床边的椅子上。
“小姑娘,谢谢你来看我们家小天。”许艳翘起二郎腿,像个女主人一样,笑眯眯地看着李雪,“不过呢,我们家小天伤得挺重,需要静养。这地方也挺乱的,你一个女孩子家,不安全。心意我们领了,没什么事儿,你就先回去吧。”
“嫂……嫂子,您别误会,我……”李雪急得眼圈都红了,“我就是想来感谢天哥的救命之-恩。要不是他,我昨天……”
“哦,救命之恩啊。”许艳打断了她,拉长了音调,“那这恩情可就大了。小妹妹,你看我们家小天为了救你,身上挨了好几刀,现在跟个废人一样躺在床上。你说,这救命之恩,你打算怎么报啊?以身相许啊?”
“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!”李雪被她这番话说得又羞又气,“医药费……医药费我来出!”
“医药费?”许艳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,她站起身,走到李雪面前,伸出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,轻轻勾起李雪的下巴。
“小妹妹,你真可爱。你觉得,我男人差你这点医药费吗?”许艳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,“还是说,你想用钱来买断这份恩情,以后好跟他撇清关系?”
“我没有!”李雪终于忍不住,眼泪掉了下来。
“没有?”许艳的笑容更冷了,“那你想怎么样?天天往这儿跑?孤男寡女,共处一室?让我男人看着你这张清纯的小脸,再想想我这个黄脸婆?然后让他良心发现,踹了我,跟你双宿双飞?”
“你……你胡说!你不可理喻!”李雪气得浑身发抖,转身就想跑。
“站住!”许艳突然厉声喝道。
李雪被吓得停住了脚步。
许艳走到她面前,收起了所有的笑容,一字一句地说道:“小姑娘,我不管你是什么心思。记住,这个男人,是我的。从头到脚,从里到外,都是我的。你要是真想感谢他,就离他远一点,别给他惹麻烦。懂吗?”
说完,她不再看李雪,径直走回床边。
李雪站在原地,呆滞了几秒钟,然后捂着脸,哭着跑了出去。
“你这是干啥呀!”王啸天看着这一幕,有些无奈地苦笑道,“人家一个小姑娘儿,让你给怼得都要哭了。怎么着,吃醋了?”
“我呸!”许艳吐了王啸天一口,傲慢地说:“论模样,论身段,我许艳怕过谁呀?我就是让她知道知道,谁才是正宫娘娘!而且就你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杨这样?!老娘昨天嘬的嘴都麻了你都没反应,切”
“那可不一定,没看我嘴还能用?”王啸天不服地伸了伸舌头。
“你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咬掉了?”许艳故作凶狠。
“过来吧你。”王啸天一把将许艳扯倒在病床上,捏着她的脸说:“来呀,给你机会,现在就让你咬。”
“切,你想得美,留着你那舌头老娘还要用呢!讨厌,刚下去点劲你又撩拨老娘,信不信现在坐你脸上淹死你。”许艳一点都不害臊。
小两口像是情人一样,打情骂俏了一阵子,至于李雪的出现,都默契地没再提。
“今晚,你带队?”王啸天终于聊上了正题。
“必须我带队。”许艳露出了霸道的一面,“马大嘴不是要你一个人去吗?行,我就替你去!我倒要看看,他敢不敢动我!”
“不行!”王啸天立刻反对,“这太危险了!他是个亡命徒 “你去叫人弄个轮椅,我打不了仗,但我必须到场,这是一种底气。”
“好!”
许艳也不废话也不劝阻,非常听话的,按照吩咐扭着大屁股出去找轮椅去了。
晚上八点多。
许艳推着满身纱布,伤口还在渗血的王啸天,来到了游戏厅的门前。
此时,门前的空地和街道上,黑压压的全是人,远不止早上那几百号,几乎整个西大街的年轻人都来了。
杨大春选出的那十个“敢死队员”,穿着统一的黑色夹克,手里提着锃亮的杀猪刀,站在最前面,气势逼人。
而他们的身后,是几百个手持棍棒、铁锹、甚至菜刀的“预备队”,一个个群情激奋,都想跟着去。
“天哥!”
“天哥来了!”
一见到王啸天来了,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了起来,自发地让开了一条路。
杨大春快步上前,激动地说:“大嫂,兄弟们都想跟着去,拦都拦不住啊!”
“不能都去!”许艳还没说话,坐在轮椅上的王啸天先开口了,他的声音虽然虚弱,但却异常清晰。
“为什么啊天哥?”
“是啊,人多力量大!咱们一起去,把大铁桥踏平了!”
众人不解,纷纷叫嚷起来。
“都他妈给我听好了!”许艳接过话,对着所有人喊道,“马大-嘴跟咱们下的是道上的战书,是十对十的局!咱们要是去几百号人,就算赢了,传出去也是以多欺少,不讲规矩,以后在吉林市还怎么抬头?再说了,几百号人上街火拼,警察能不管吗?到时候咱们全他妈得进去唱《铁窗泪》!都想进去蹲大牢吗?”
这话一出,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“今晚,就我们这十二个人去!”许艳指了指那十个敢死队员,以及自己和身后的浩子,“我们是去赴宴,去给天哥挣回面子!你们,都给我留在西大街,看好咱们的家!”
紧接着许艳走到那十个“敢死队员”面前,将自己手中那个碎酒瓶递给了为首的大迪。
“今晚,你们十个,加上我,还有浩子,我们十二个人,就是西大街的十二把尖刀!我们去,不是为了打赢,是为了告诉马大嘴,告诉整个吉林市——”
她深吸一口气,转过身,面对着轮椅上的王啸天,也面对着身后那几百双狂热的眼睛,用一种近乎燃烧生命的激情,嘶吼出最后的战前宣言:
“西大街,没有孬种!”
没有孬种!
没有孬种!
数百人的怒吼,汇成一股冲天的豪气!
就在这气氛被推向最高潮,所有人都热血沸腾、准备目送英雄出征的悲壮时刻——
“咳咳!”
一声不合时宜的咳嗽声响起。
只见杨大春,不知什么时候又爬上了那把破椅子,他背着手,迎风而立,脸上带着一种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深沉表情,用他那自以为充满磁性的嗓音,高声吟诵了起来:
“西街好汉十二人,
今夜踏月去平坟!
刀光剑影浑不怕,
只为天哥……一个人!”
诗,是好诗……才怪!
这首狗屁不通、平仄不分的打油诗一出,全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。
那股刚刚被点燃的、冲天的豪气和悲壮感,就像被一泡尿给浇灭了,荡然无存。
所有人都用一种看傻逼的眼神,目瞪口呆地看着站在椅子上、还沉浸在自己“文采”中无法自拔的杨大春。
“我操……这傻逼又犯病了……”
“妈的,好好的气氛全让他给毁了!”
“真想给他一酒瓶子……”
人群中传来一阵压抑不住的、充满嫌弃的暗骂声。
就连坐在轮椅上的王啸天,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,虚弱地骂了一句:“妈的……智障……”
许艳更是气得差点把手里的碎酒瓶扔到他脑袋上。她深吸一口气,懒得再理这个活宝,对着浩子和大迪一挥手:
“出发!”
马达轰鸣,车灯划破黑暗。
在数百名兄弟哭笑不得、想骂又不敢骂的诡异气氛中,十二个人,十二把刀,尴尬而又不失决绝地,冲向了那片未知的、血色的黑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