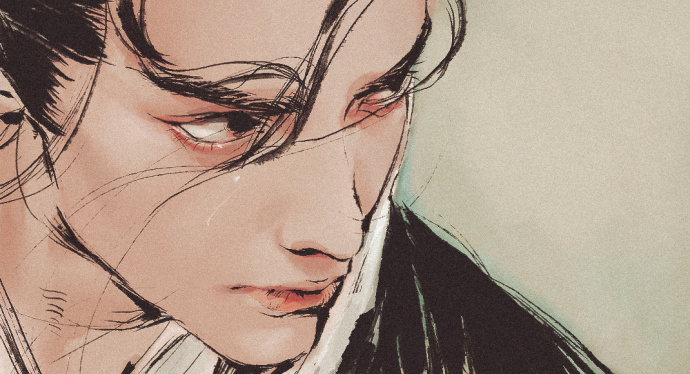028 他不能服
这天上午,茉莉又来了,这次空着手,坐在炕沿儿上就开始抹眼泪。
这丫头没有百合淡雅,身材也赶不上牡丹,可最有女人味儿!
不然也不会住天字一号房。
说到女人味儿,有些玄妙,怎么说呢?
就是每次一看到她,某个六道沟的犊子都会蠢蠢欲动,想把这小妖精就地正法,想象着她在身下梨花带雨连连求饶。
上次的‘鼻血’事件,这妖精就利用他赚了整整十块大洋,所以唐枭再动心,也要防着她使坏。
“妹子,怎么了?”唐枭捏住了她柔若无骨的小手,柔声劝着:“别哭啊,哭得哥心疼死了……”
“枭哥,我、我要离开这儿了!”茉莉哽咽道。
唐枭一怔,忙问什么情况。
“吉江电影茶社的朱老板要赎我……”
朱文泰?
唐枭脑海里出现了他的样貌,去年那晚赛秋香来百花楼闹事,这位朱老板就在茉莉房间了,很英俊的一个小伙子。
“那挺好啊,年轻,英俊,又有钱!”他说。
茉莉哽咽着:“他有老婆,赎我也是外室做小,而且……而且……人家……”
“说呀,啥呀?”唐枭急了。
“人家、人家喜欢的是你……”
“……”
“傻样儿!”她扬起小拳头打在了唐枭胸口上,随后红着脸探过身子,把俏生生的小脸蛋儿贴在了他脸上,在耳边吐气如兰:“枭哥,人家喜欢你,真喜欢你,每晚辗转反侧都是你,梦里也是你……走之前,人家想把身子给你……行吗?”
脸上感受着她的火热,鼻子里满是幽香,耳朵里也是甜言蜜语,要不是闭着嘴,唐枭的小心脏一准儿能从嘴里蹦出来,跳到房檐儿上去。
“那个……行、行吧?”他结巴起来。
茉莉坐了回去,俏脸绯红,低着头不敢看他,小声说:“我、我回去洗洗……等你……”
唐枭连忙拉她:“不用,在我这儿就行!”
茉莉猫一样起身躲了过去,瞥了一眼炕上油叽叽的高粱秆炕席,绕着手指,扭着身子说:“不行,你这……你这不好,你快点儿!”
说完,花蝴蝶一样往外跑。
唐枭拍着炕席喊:“别走啊,干净,不扎屁股……”
人已经跑出去了。
幸福来得太突然了,唐枭就觉得脑袋瓜儿‘嗡嗡’地,光着脚丫子兴奋地在炕上走来走去,边走边搓手。
人家回去洗澡了,自己是不是也该洗洗?
抬起手看看,再算计一下时间,应该有六七天了吧?
没事儿,拆开!
拆开棉布,凑到窗前仔细看,那拨浪鼓一样老大夫家里的红伤药确实厉害,真好利索了!左手虎口处和食指内侧只能看到几条不规则的细线,看着像蜘蛛网一样。
随后,他开始翻炕勤,找出了一套干净的箭袖黑棉布短褂,还有双去年秋天买的千层底儿布鞋。
刚要下地,又愣在了那里,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三姐时的情形,还有她的那句话:先说好了,要是发生‘陪柜’ 的事儿,老娘就把他给煽了!
不对!不对!他用力摇了摇脑袋,‘陪柜’是强迫,自己和茉莉你情我愿,算哪门子‘陪柜’?
再说了,茉莉就要离开百花楼了,这么好的姑娘,能让她带着遗憾离开吗?
不能!
绝对不能!
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?!
刹那间,这位从大兴安岭六道沟进城的犊子觉得自己高大伟岸起来,连忙蹦下地,趿拉着鞋跑出去打水,简单洗了洗某处,就着水把脚也洗了。
兴冲冲穿戴利索出了门,迎面见到三狗,忙问:“看见老陈了吗?”
“和三姐上街里了,枭哥,你也要出去?”三狗问。
“那个……我问个事儿!”
“啥呀?”三狗见他一脸神秘,也很好奇。
“你听说没有,就是吉江茶社的朱老板,听说他要赎茉莉……”唐枭并没有被突来的幸福冲昏头脑,那小妖精一个屁俩谎,必须打听清楚了才行,可惜陈大茶壶和三姐没在家。
其实他很清楚,三姐说阉了自己是扯淡,他是怕这件事情成了以后,陈卫熊不高兴。
三狗想了想:“前段时间好像听说过,而且朱老板确实很喜欢茉莉姐,每次来都去她房间,可具体什么时候赎,我还真不知道……枭哥,你问这个嘎哈?”
唐枭这才安下心来,看来果然是要离开了,他感觉自己肯定脸红了,摆摆手说没事儿,低头就走。
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,三狗挠了挠光头。
站在天字一号房门前,这刁民贼一样左右瞅了瞅,还没到中午,姑娘们应该还没起床,院子里安静的能听到微风的声音。
咚咚咚!
他敲得小心翼翼。
里面响起茉莉的声音:“是枭哥吗?”
“嗯……嗯呐!”
“进来吧!”
吱呀——
唐枭推门进屋,又连忙关上,还反手插上了门闩。
院子里的姑娘们都住套间,外间用来招待客人,格调高雅,雪白的墙壁上错落有致地悬挂着名家字画,墨香与时光交织,营造出一种超脱尘世的雅趣。
中央一张红木雕琢的八仙桌,沉稳而庄重,配以成对的官帽椅,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古典韵味。
右手侧还有张软榻,这是用来招待客人抽大烟。
茉莉的声音从里屋传来:“枭哥,你先上床等我一会儿……”
唐枭听到了水声,小心脏又开始胡乱蹦跶起来,一边脱衣服,一边往里走,嘴里还说着:“妹子,不急,用不用我帮你搓搓背?”
走进卧室,水声从屏风过来传来,热气顺着屏风的缝隙往出荡漾。
他也荡漾起来,连忙扒掉最后的大短裤,蹦上了大床。
真香!
还不等他扯被去盖,屏风开始往一侧收拢,茉莉和牡丹、百合三个人穿戴整齐,背着手笑盈盈看着他。
身后木盆里的水,热气腾腾。
唐枭蒙了,紧接着大吼一声:哎呀我艹!人像被蛰着一样蹦了起来,百合连忙捂住了眼睛。
唐枭跳下床就往出跑,还没忘了捡起地上丢弃的衣服。
身后的茉莉她们往出追,开心的叽叽喳喳,很快又安静下来。
唐枭根本顾不上看她们了,站在门口慌里慌张套裤子,恨恨骂道:“茉莉你个小妖精,早晚有一天哥把你按我炕上……还有牡丹、百合,你俩等着!”
他跑了,后面三个女孩儿面面相觑。
百合一双美目难掩惊愕。
牡丹喃喃道:“怎么会这样?”
茉莉犹豫了一下,问:“能不能是被哪个衙门抓过,严刑拷打弄的?”
百合摇了摇头:“不对,那是野兽抓的!”
原来,刚才唐枭往出跑的时候,整个身体都被三个人看得清清楚楚,尤其是后背。
这个男人瘦削如松,后背更是一幅活生生的战斗地图,横七竖八地交错着各式各样的伤痕,或深如沟壑,或浅若细线。
这些伤痕有些狰狞可怖,又似乎隐藏着几分不屈与豪迈,如同古老图腾,诉说着曾经的荣耀与坚韧!
“不管了,反正你俩都看到了,拿钱!”茉莉笑吟吟地伸出了手。
之前说好的,她要是能在一个时辰内,让百合和牡丹看到枭哥的光屁股,一人输五块大洋!
如果没成功,她一人输十块。
牡丹是真想看,百合就是想赢回上次输的五块钱。
枭哥衣冠不整地从天字一号房跑出来的事情,不知怎么就传开了,而且还越传越夸张,有人说光着脚鞋都没穿,有人说扯淡,明明是光着腚……
当天晚上,陈大茶壶就把他一顿骂,骂得这犊子臊眉耷眼,没好意思回嘴。
后半夜,两个人躺炕上以后,陈卫熊问:“真光腚了?”
“……”
第28章 鲍里斯
这事儿闹的,枭哥哥在百花楼又一次扬了名儿。
第一次,是秋实阁的老鸨子赛秋香来砸场,他一个人连捅了13个;
第二次,是抓到了扒厕所的黄四儿;
第三次,是今年的正月十五晚上,青帮张七爷的徒弟白回子砸场,他剜下了一块自己的肉;
这是第四次,光着屁股从天字一号房跑了出来!
唐枭说他冤枉,说自己明明套上了裤子,可没人听他解释。
还有人说,枭哥想与茉莉鱼水之欢,可茉莉姐坚决不从,拎着炉钩子赶他出去的。
挨了陈大茶壶一顿骂,本以为三姐也得找他,没想到人家根本没当回事儿,院子里遇到几次,笑得一脸暧昧,笑得唐枭都想扒条地缝钻进去。
不只三姐笑,就连二黑、栓柱和海棠他们也笑,没两天,就把这犊子笑去了斜对过的鸿福茶馆。
茶馆有说书先生,唐枭觉得这儿挺好。
来壶碎茶,听几段评书,比在院子里被这些犊子们笑自在多了。
茶馆老旧木门半掩着,十几张方桌摆得满满当当,客人们或坐或立,茶气蒸腾。
墙上挂着几幅褪色的字画,勉强辨认出是山水与花鸟。
前面矮台上的说书先生长袍马褂,手拿折扇,滔滔不绝,不时还配合几个手势,引来众人哄笑或惊叹。
几个要饭的熊孩子爱扒窗沿儿听书,总被花子头儿拧着耳朵扯走。
桃花巷行人匆匆,茶馆内时间仿佛静止,只有茶香与说书声交织,勾勒出一幅生动画卷。
唐枭自得其乐,在这儿待着,报纸都不用看,什么社会新闻和小道消息都能听到,真真假假,有点儿意思。
街面上一些小混混也常来,没钱喝茶,唐枭就请他们,一来二去也都熟悉了。
他是百花楼的人,又是名声在外,这些混子甭管多大年纪,一个个见面都点头哈腰地喊枭哥。
旬五还在养伤,高力士每次夜里过来,都带着五六个人,腰间鼓鼓囊囊藏着手枪。
两个人在海棠房间或是把酒言欢,或是对弈一局,很是悠闲。
陈大茶壶讲给唐枭的,几乎都是江湖上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,什么明八门暗八门,南北春典以及各地有名气的大亨强豪。
这让他开阔了眼界,长了不少知识。
而高力士说的都是哈尔滨本地的事情,从青洪帮说到东震堂,还有各方势力的爱恨情仇,地盘的划分与争斗。
这让唐枭更加充分地了解了这座鱼龙混杂的城市。
他没问那100支枪卖没卖,卖给谁了,高力士也始终没提。
天气渐渐热了。
这天下午,茶馆里都在说,五天前北京城发生了什么学生运动,哈尔滨临时警察局教练所的学生积极响应,还开大会发表演说。
很快,就有三个学生被开除,好多同学激于义愤,纷纷退学。
听了半天,唐枭也没弄明白这些学生不好好上课,跟着瞎在折腾什么。
学生的事情说完,又开始议论起卢布,说张大帅要发行一种新国币,以大洋为本位,票面上还会印有‘哈尔滨’字样。
毕竟还都没见过,有人说不太可能,卢布都这个奶奶样了,新纸币更好不到哪儿去,到啥时候还得是袁大头值钱;有人说大洋不方便,还得是老头票儿……
几个老爷子争论的面红耳赤。
后半夜关门以后,陈卫熊弄了两个小菜,哥俩盘腿坐在小炕上又喝了起来。
唐枭说:“下周老高又有一批货,还想让咱俩跑!”
“好事儿呀,没涨点儿?”
“没问,我琢磨着,咱能不能贿赂一下九站码头的老毛子!”
“也不是不行,可这些人如果知道了是军火,肯定狮子大开口。”陈卫熊说。
唐枭说:“这个我想过,可闯关风险太大,折一次就是几千现大洋,别说咱哥俩赔不起,高力士也得闪着腰!稳妥一些的话,哪怕少赚一些,还是要把码头这条路打通了!”
“走高力士的通道呢?他在头道街码头可是如履平地!”
唐枭夹了口凉拌土豆丝,摇了摇头:“那毕竟是他的关系,不是咱们的,你说呢?”
陈卫熊笑了,这小子,终于开窍了!
“你想怎么做?”他问。
“明晚请那个大胡子去秋实阁!”
陈卫熊愕然:“为啥不来咱这儿?”
“一是不想让栓柱他们知道,二……”他没继续往下说。
陈大茶壶叹了口气,喝了口酒才说:“兄弟,窑姐就是窑姐,就算真钻了被窝,也别钻心里去,明白吗?”
唐枭怔怔出神,好半天才说:“哥,你说这世道,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安居乐业?”
“不知道,估计咱们是看不到了,看看洋人那些玩意儿,人家在造枪造炮造火车,咱们还在玩弓箭骑牛马,还说洋人是奇技淫巧!这一差起码差出去大几十年,没有两三代人,可追赶不上……”
唐枭一口干了杯中酒,胸口似乎有什么堵着。
陈卫熊岔开了话题:“你小子捅了他们那么多人,还敢上门?”
唐枭呵呵笑了:“那帮小子每次在街上看到我都躲着走,这次我亲自上门,正好看看什么反应,多有意思!”
陈卫熊笑着摇了摇脑袋,到底还是年轻人,不过他觉得也挺好,唐枭已经在桃花巷有了些名气,再去挑衅一下,未必是坏事。
又问:“为啥不直接请那个当官的大胖子呢?”
唐枭说:“当官的肯定不会天天守着关卡,做事情的还是下面的人!慢慢来,咱们现在这个体量,先把下面人的关系搞好就行,什么时间方便过关,自然会告诉咱们。我现在犹豫请一个还是请俩,又怕请不动他们,找什么借口呢?”
陈大茶壶笑了:“就请一个,其他人怎么分钱和咱们没关系!也不用找借口,就说请喝酒,那些老毛子肯定屁颠屁颠跟咱走!”
“……”
第二天下午,两个人穿戴整齐,来到了埠头区的九站码头。
有船靠岸,好多旅客往出走,多数都是外国人。
两个人低着头混进人流往里走,可因为逆行太显眼,很快就被两个守卡的大兵拦下了。
陈大茶壶连忙点烟,点头哈腰地说来找人。
结果烟抽了,还是不让两个人进去。
旅客都快走光了,眼瞅着那个大胡子就站在三十几米外,唐枭急了,扯着脖子喊:“哎——大胡子,我来请你喝酒的!”
卫兵端枪怼他,嘴里骂骂咧咧。
陈卫熊连忙解释:“我们是那个大胡子的朋友,过来请他喝酒,不信你去问问他?”
士兵狐疑起来,和另外一个士兵嘀咕了几句,跑向了大胡子。
两个人说着什么,大胡子往这边看了看,很快就跟着卫兵过来了,冷着脸用俄语问:“我不认识你们,你们要干什么?”
陈卫熊指了下唐枭,也用俄语说:“上次我的伙计手被割伤了,您还记得吗?”
大胡子恍然大悟,换成了汉语:“对对对,我记得他,怎么了?”
“上次给您添麻烦了,我们想请您喝顿酒,您看方便吗?”
“喝酒?”大胡子眉飞色舞起来,“我要喝你们流子上的纯粮烧酒,要60度的!”
他说得十分生硬,不过唐枭还是听明白了,没想到这家伙一听到酒就像换了个人,连忙赔笑说:“有有有,不止有酒,还有姑娘!”
“哈拉少!什么时候喝?”
“晚上几点方便?”陈卫熊问。
“五点我交接班!”
“好,我们来接您!”
晚上两个人准时来接上了大胡子,雇了黄包车,直奔傅家甸桃花巷。
三辆黄包车拉成了一排,陈卫熊示意黄包车夫慢一点,等后面的车上来以后,对大胡子说:“我姓陈,该怎么称呼您?”
“叫我鲍里斯就行!”
陈大茶壶竖起了大拇指,笑道:“好名字,为了荣誉而斗争!”
鲍里斯有些吃惊:“喔——?!陈,你一定是我们俄罗斯的好朋友,竟然知道我名字的含义!”
过后唐枭问起这件事,陈卫熊直撇嘴,说这些老毛子翻来覆去就那么些名字,什么亚历山大、安德烈、丹尼尔、马克西姆、安东、康斯坦丁、斯米尔诺夫……时间长了,傻子都能记住了!
三辆黄包车停在了秋实阁门口。